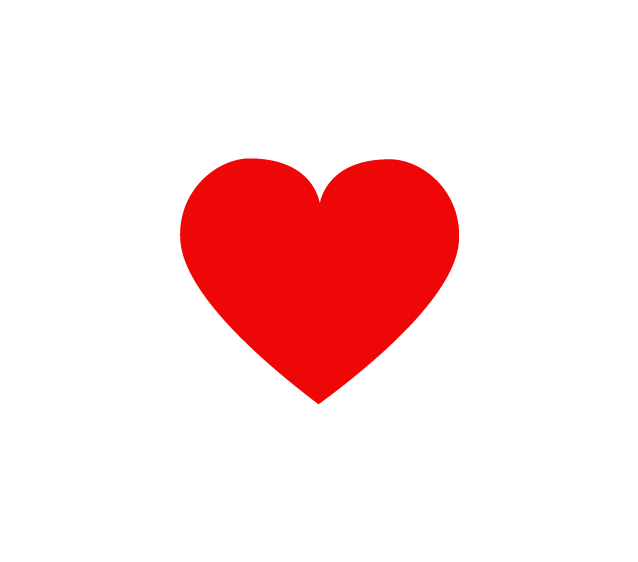在时下的舆论场中,第三次分配的热闹与公益慈善的冷清,形成了一组值得玩味的对照。第三次分配本只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功能和价值之一,近来却因为一再出现在官方会议场合和政策文件中而得到普遍关注,其影响力已溢出公益慈善的范围,颇有喧宾夺主之势。甚至由于二者总是并列出现,加之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外延不断拓宽,第三次分配近乎成为公益慈善的代名词。学界也乘势跟进对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内涵、基础理论、实践领域、作用发挥机制等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一波研究高潮。
第三次分配是基于道德、伦理、同情、信念,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募集和捐助等形式,对社会资源和财富所进行的分配过程。在官方文件或学界研究中,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被有意无意设定为富裕群体,“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希望他们在道德驱使或文化感召下,通过捐赠和资助参与分配,以缓和收入差距,解决社会不平等,助力共同富裕进程。
然而,第三次分配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不平等?富人、中产、穷人,哪个群体为第三次分配所做的贡献更大?富人群体参与三次分配的背后动因,真的是道德感吗?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第三次分配在公益慈善事业中的角色?这些关于第三次分配的前提性问题的答案,绝非不言自明的。
一、热闹的假象:第三次分配能缓解多少不平等?
第三次分配能缓解社会不平等吗?毫无疑问,能。进一步,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呢?很遗憾,微乎其微。
一方面,从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资源总量看,作为慈善“典范”的美国,其慈善捐赠总额绝对数量与占GDP的相对比重,都位列世界第一。根据Giving USA 2024报告,2023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预计达5571.6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比重约为2%。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国历年慈善捐赠占比在起伏中持续上升,这已经是历史最优成绩,且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即便如此,其所占比重也是相当微小的。
在中国,根据《2020-2021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2020年中国慈善捐赠为1534亿元,占当年GDP比重约为0.15%。即使是纳入志愿服务贡献价值和彩票公益金后的最广义口径的慈善资源,其总额也不过将近4500亿,占比不到0.5%。更何况,彩票的主力购买者往往是心存侥幸,寄希望于运气改变生活的社会底层群体,他们所贡献的“慈善资源”与其说是第三次分配,不如说是一种逆向分配。
另一方面,从第三次分配的资源流向看,其“慈善性”并不容乐观,Giving USA 2022显示,2021年1357.8亿美元的捐赠流向了宗教领域,“满足基本需求”项目所获的捐赠是最少的,真正用于弱势人群救助和社会福利的并不多。反倒是在中国,根据中国慈善捐赠报告,大额捐赠资金都流向了医疗健康、扶贫开发、教育救助等可能更多惠及弱势群体的领域。
进一步看,现代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私有制及建筑于其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各国的工资和税收等政策,则决定了收入在资本、管理才能、劳动力、土地和技术等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格局。颇为吊诡和反讽的是,越是新自由主义风气更为浓重的国家,其劳动收入分配不平等也越严峻,而其慈善事业也是最为发达蓬勃的。根据托马斯·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前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从5%-9%显著上升至10%-20%不等,相比之下,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则基本没有变化。而根据OECD的数据,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其社会支出中的私人支出占比,也恰恰名列前茅。
这并不难以理解,慈善捐赠和三次分配,本质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自我矫正。因此,慈善事业在新自由主义最为浓重的地方发展最好,也并不为奇。这提示着我们需要对第三次分配保持审慎,因为即使是最为成功的慈善事业,其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功效,也不过是资本主义肌体上的一片创可贴,无助于掩饰更无法治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巨大脓疮。收入分配不平等,终究要靠改善第一次分配和强化第二次分配来予以解决。
二、异化的标准:哪个群体为第三次分配贡献更多?
富人是慈善捐赠和第三次分配的主力,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马修·比索普和迈克尔·格林那本名为《慈善资本主义》的书,其副标题便是“富人如何拯救世界”。新闻媒体上的富豪捐赠新闻,研究机构所做的捐赠排行榜,官方或民间颁发的各式捐赠奖项……都强化了此种印象。
但事实上,在美国,2021年的总计3268.7亿美元的个人慈善捐赠中,“巨额个人捐赠”约为150亿美元,仅占5%。但富豪们却因此收获了远高于其捐赠额度的曝光度、美誉度和道德优越感。而且,这种个人捐赠往往也是与其企业经营等关联其在一起,有助于其获取良好声誉,修复企业形象,开拓市场份额,减少研发成本,提升招聘优势、提升员工忠诚等实利。如果再考虑到屡见不鲜的“诺而不捐”现象,富人捐赠实在是一门费效比极为可观的生意。
反之,普通人为公益慈善做出了更为实在的贡献,却只收获了与之并不相匹配的关注。根据美国联合经济委员会所出的《改革慈善捐助的税收减免》(Reform the charitable deduction)报告,在捐赠额度与收入水平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倒U型关系,中低收入群体的捐赠占比在3.3%-4%之间,而中等和中上收入群体的捐赠占比反倒下降至2.4%-3.2%之间;而且,考虑到税收扣除,收入占比后20%的群体,其100美元的名义捐赠,实质捐赠为99.8美元,从税收优惠中所获甚微;但前5%群体,其100美元的名义捐赠,实质捐赠仅为78.7美元,这个数据在前1%群体处,更是下降到70.9美元,收入顶尖群体享受了大部分的税收折扣,也收获了大部分的慷慨美名。
在同一份报告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低收入者比中高收入者更倾向于捐赠“满足基本需求”的项目,同样,此类项目近一半的资金,也源于低收入者的捐赠。因此,他们的行为,实则更接近“慈善”(charity)一词扶危济困、怜恤弱者的本义,但所获的慈善奖项、报道和研究却又不成比例。
更有甚者,许多实际上的慈善和第三次分配行为甚至被排除在“慈善”之外。比如近些年势头强劲的水滴筹、轻松筹等个人求助网络平台,所筹集的善款已经接近千亿元,这些资金,大多也来自普通的社会公众,也切实帮助到了困境中的弱势者。
此外,在村社、学校、单位内部,各式各样的互助行为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这些自发的、传统的、个体化的善行生机勃勃,肆意生长,创造了难以估量的繁盛,发挥着重要的第三次分配作用,但因其指向“确定的少数”而非“不确定的多数”,便不被主流定义和规范所认可。
或许我们应该正视这一悖论,那就是志在解决社会不平等的慈善和第三次分配内部,其实存在巨大的歧视和不公,而这种歧视和不公的受害者,同样是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利位置的弱势者和普通人。
三、存疑的动机:道德感是富人捐赠的主因吗?
伦理道德自然是富人捐赠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富人捐赠的动因更是多元而复杂的。保罗·瓦莱利在其《公益:从亚里士多德到扎克伯格》(Philanthropy: From Aristotle to Zuckerberg)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使在没有税收扣除的传统社会,慈善也同样是作为身份象征和“符号资本”而存在,发挥着对内界定同类,对外区隔他者的作用,而非纯粹出于道德感和责任感。
而在有了税收减免政策的现代社会,避税或许成为了富人捐赠的主因。《慈善捐赠与税收政策:历史与比较视角》(Charitable Giving and Tax Policy: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一书对美国1915至2005年间,前万分之一顶尖高收入群体的捐赠力度与美国实际边际税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发现两条曲线高度重合。前述《改革慈善捐助的税收减免》报告也指出,在2018年,美国慈善捐赠的税收减免总额达541亿美元,其中75%均由收入前5%的家庭获得,56.4%由前1%的家庭获得。
此外,正如皮特·巴菲特在纽约时报所撰之《慈善工业综合体》(The charitable-industrial complex)一文所指出的那样,一些富人的慈善行为,与其说是回馈社会,不如说是为了“漂白良心”,为的是借此赎买到自身的心安。事实上,回顾资本主义慈善史,我们便会发现这种“用两只手捐赠,但用更多只手掠夺”的案例比比皆是。钢铁大王卡耐基撰写的《财富的福音》在今天被奉为慈善圣经,但其发家过程充斥着贿赂、威胁、恐吓、垄断和秘密交易;洛克菲勒基金会以“促进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福祉”为使命,而其创始人正是臭名昭著的勒德罗大屠杀的制造者;斯坦福大学的捐建人利兰·斯坦福,在太平洋铁路修建过程中非法雇佣并剥削数以万计的劳工……
最后,富人将资金捐赠给自己控制的私人或家庭基金会,设立慈善信托,看似转移了所有权,实则依然保留了支配权。他们通过基金为家人或朋友提供赠款,向政客或政治组织给予支持,发挥并且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正如皮凯蒂在其著作《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中批判的,慈善事业缺乏参与性和民主性,针对慈善捐赠的税收减免,实际上是中下阶层用自己的税收补贴了富人的慈善偏好,赋予了富人在界定公共利益、分配公共物品方面更大的权力。
总之,正是资本主义结构制造了社会不平等,而处于这种结构优势地位的群体既不愿,也无法,也并未解决不平等。改善收入分配,是公益慈善和第三次分配所不能承担的重任。
结语:让第三次分配归其本位
上述辨析并非为了贬低第三次分配和公益慈善事业,而恰恰是为了让其复归本位。在收入分配的配套制度安排中,第三次分配处于拾遗补缺、锦上添花的辅助性位置,对此我们当有清醒认识;而在公益慈善的价值和功能定位中,第三次分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但也绝非唯一。
公益慈善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复合功能,比如在政治和治理方面,公益慈善组织可以协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作为社会力量制约公共权力、参与公共治理;在经济商业领域,社会组织有助于遏制市场暴政,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践行商业伦理的重要伙伴;在社会文化领域,公益慈善是构筑社会资本、推进社会自治、满足结社需求、传承弘扬文化的重要阵地;在科学技术领域,慈善捐赠也是提供更为宽松、灵活资金,激励基础科学和“冷门绝学”研究,促进长期科学进步的独特力量……
为热闹的第三次分配降降温,让喧嚣的学术和舆论场在此议题上沉静稍许,我们才可以合理定位第三次分配和公益慈善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各自角色和功能,让它们承担起它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发挥出它们可以发挥的作用。